
话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每次看到或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起了自己的读书“声”活。读书出声,那读书之声,不仅入耳,而且也入脑了。
读书出声高潮期,是我参加高考的前夕。
1980年,父亲单位的局机关决定从北矿迁移至南矿,新建办公楼选址就在距我家百十来米的地方。
高考前一个来月,班主任老师时不时地就对我们说,“你们很快就要‘七·七事变’了,加紧读书复习啊!”那时的高考时间是每年的7月7日,这个时间与历史事件“七·七事变”同日。这让我们格外努力。
每天早晨六点半不到,我就坐在客厅兼厨房餐厅的房子里读起了语文书。但是,同我一道早晨读书的还有我的弟弟和妹妹。这样“交响声”地读书,互相有影响;我更怕影响到邻居,因此就压着声音不敢大声读。总觉不过瘾。
上下学途径父亲单位这栋已建好框架还没有进行内外装修的办公楼时,我突发奇想,早晨到这办公楼顶上读书,既空气好,又安静,即使放开嗓子读书,也不影响任何人,那多过瘾,那多效果好。想到这,我心里一阵喜,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得意。
想到就干。我和父亲说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父亲很是赞成。母亲则交待我要注意安全。
办公楼处在半山腰中,左侧和后部靠山,前面则是大斜坡,一片空旷。
每天早晨我手拿语文书和历史书从家里径直走到那办公楼的顶部六楼,高高在上,放声大读,甚是过瘾。语文书中杜甫的那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犹被我喜欢。4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还有较深的印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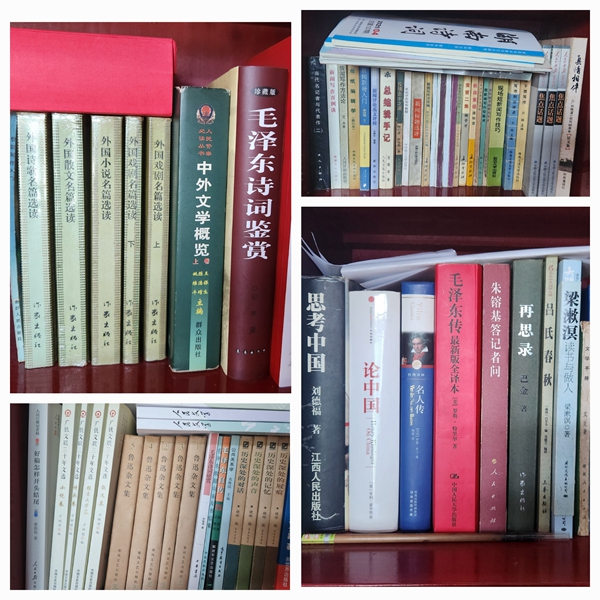
参加工作几年后,我干上了列车乘警工作。在这个“移动世界”里,我又突发奇想。心想,在奔跑的列车上读书,车轮声伴读书声,让闲时不闲。
于是每次出乘上车前,我始终记得在自己的乘务包里放上一本书,用于在晚上下班后阅读。
我值乘的是开往北京的车,晚上10点半下班后,列车是在中原大地奔跑,那飞转的火车车轮在钢轨上不知疲倦地转着,发出特有的金属声。在这金属声中,我的夜读开始了。
我读书是在宿营车。铁路人叫休息车。夜晚时,休息车内光线更暗,只有微弱的廊道灯亮着,乘务员都在睡觉。我站在休息车和机车相连的那端边门口处。顶上有灯很亮,和车厢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中间的通过门隔着玻璃可以看到牵引我们这趟车向前奔跑的机车。两侧边门口玻璃外面是不停闪过的黑夜世界。脚底下,不断响着车轮与钢轨面摩擦的金属声。就是在这种车轮声里,我别有洞天地、自顾自地读起了自己心爱的书。读到一句精彩话语,或是读到一段精彩对话,我便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
冬天,在边门口处这个“无人”的地方没有暖气,且因为门闭合不严,还有微微的冷风吹进来,这便更降低了连接处的温度。晚上10点半下班后,我坚持站在这个较冷的连接处看两个小时的书。在两个小时的读书结束后走近暖和的车厢内,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双脚已由先前的热脚变成冰脚了。
连接处冬天没有暖气,同样,夏天的连接处也是没有冷气的。看个把小时书就热得流汗了,这时我就打开门让连接处里进点冷气,或移几步往车厢内走,站在有冷气的狭小的茶水间处继续看书。身感凉了,汗止住了,则又到边门口处那“斗室”里看书。
冬天冷夏天热的,有乘务员就关心地对我说,“到我乘务间里坐着看嘛。”“站着看看得还认真些,效果还好些。”我则总是笑着回答乘务员。
德国作家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车轮声伴着读书声,20多年时间我在车轮声里“认识”了很多思想高尚的人,这让我又像孩提上学时受到了老师的教育一样,身上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车轮声推动了我的读书声。
(怀化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 飞燕)
(编辑:李凌)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64号 京ICP备18014261号-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659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64号 京ICP备18014261号-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6597号



